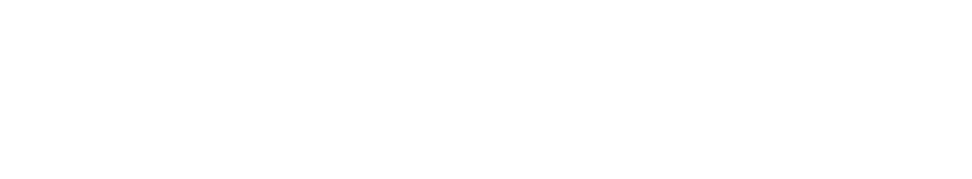应崇福(1918-2011),浙江宁波人。1940年毕业于华中大学物理系,1945年获西南联合大学清华研究生院硕士学位,1951年获美国布朗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。曾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。物理学家、超声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国超声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。

回到祖国,开创我国超声学研究
1941年,应崇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。谈到在西南联合大学上学时的经历,他曾经描述为“苦中充满魅力”的岁月:“在联大,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科学的学术思维方法……更重要的是,我学到了一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!”
1948年,应崇福前往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身在异国他乡的应崇福,认为唯有好好读书,才能报效祖国,才能做到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。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,他学习异常刻苦,1951年以全A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。应崇福毕业后,立即买好船票准备回国,却接到美国移民局禁止出境的通知,被迫滞留美国。他来到布朗大学丘尔教授的金属研究实验室,在这里与超声学结下了半生情缘。1955年4月,美国开始逐步放松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限制,已成为助理副教授的应崇福谢绝了丘尔教授的多次挽留,放弃了国外的科研条件和生活待遇,于1955年11月25日毅然踏上了回国之路。他饱含深情地给丘尔教授写了一封长信:“你大概知道,有一个国家叫中国,这个国家是我的祖国……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回去,不去面对许多困难,那么还有什么人能够回去呢?”

1949年,应崇福在布朗大学
应崇福在美国从事的是超声学狭窄范围的基础研究。回国后,应崇福面对国内超声学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的情况,与同事们积极承担“两弹一星”相关的超声检测任务,同时还参与了《1956—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(修正草案)》声学部分的讨论,使超声工作成为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之一。
严谨治学,大力培育人才
在学生的培养上,应崇福一直以严谨严厉著称。一名学生在选定论文题目时,涉及一种材料的磁导率,这名学生认为只是方案论证而并非真正的论文报告,没有必要为这个数据花费过多时间,就根据书上提供的相近材料的磁学参数,做了简要讨论就断然下了结论,认为该材料的导磁率“肯定”不会大于某某值。应崇福看了很生气,当着几位老师和同学的面,严厉地批评了他:“哪来这么多‘肯定’!凡事都要自己亲自去做,说话一定要有依据、有出处,不能想当然。你的思维方法有问题,回去马上做实验!”后来,这位学生按照要求补做了实验,实测到的数据确实与原来“估计”的有差别。有的学生的毕业论文曾被他用不同颜色的笔批注得密密麻麻,五次修改才得以通过。应崇福认真严谨、一丝不苟的做事原则,深深地影响了他身边的人。
应崇福在培养年轻人时,也非常注意创造机会让年轻人扩大影响,他鼓励学生在课题组发表的论文中署名,并在申报奖励时也列上学生的名字。应崇福还指导选派了一批学生出国进修,也常鼓励年轻人多参加学术交流。在参加会议前,他组织学生们试讲学术报告,并从报告的内容、次序、详略,以及语速、用语、手势、态度等方面,都提出许多详细具体的意见,使报告的效果得到很大的改进。

应崇福(前排右三)与学生们在一起
对“真”的坚守,伴随了他的一生
无论是做科学普及还是做科学研究,应崇福始终都站在真理的一侧。
20世纪50年代末,超声一度被形容得“无所不能”,1961年还形成了推崇超声的“超声运动”。但是,在气势汹汹的“超声运动”面前,应崇福不配合,坚决不夸大超声的用处。到1961年底,为了恢复和推进超声的发展,应崇福公开发文做科普,实事求是地再次向公众讲述了超声的应用和原理。
回想起这段历程,著名声学家、物理学家马大猷曾感叹:“崇福同志可谓真科学家。”
对“真”的坚守,伴随了应崇福的一生。1991 年,中国物理学会成立 “科学家谈物理”编委会,一向热心于科普的应崇福受邀写了一本介绍超声学的小册子《超声和它的众多应用》。在书中,应崇福毫不避讳地分析了超声作为应用手段的弱点,把超声学的学科发展直观严谨地展现给公众。
1998年6月,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发起的一项跨世纪科普出版工程“院士科普书系”启动,“院士科普书系”编委会正式成立。应崇福从当年秋天开始收集材料,次年又集中在半年时间里夜以继日地写作。2002年,《我们身边的超声世界》一书最终出版,这本书的书稿,从手写版到打印版,数易其稿,反复修订,从中足以看出应崇福对于科普工作的认真程度。
(部分故事改编自倪思洁、刘逸杉、闫玮丽:《应崇福:做燃到最后依旧笔挺的烛芯》,《中国科学报》2023 年 12 月 28 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