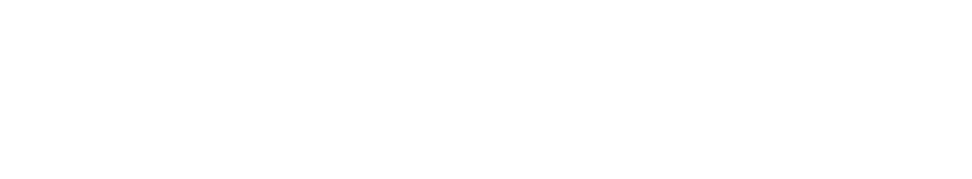马大猷(1915-2012),广东汕头人。193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,1940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曾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。声学家、物理学家和教育家,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,中国现代声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。

开创哈佛大学先例的中国留学生
在少年时代目睹祖国的积贫积弱后,马大猷便立下“科学救国”的信念。1936年,马大猷获得北京大学理学学士学位,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。后来,马大猷仅用两年时间,就获得了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(1939年) 和哲学博士学位(1940年),这在哈佛大学是没有先例的。求学期间,马大猷崭露头角,他被认为贡献了世界声学史上“波动声学的一个基本公式”,取得了令美国声学界瞩目的成就,这确立了他在现代声学研究中的地位。马大猷虽身在国外,仍心系祖国,不忘抗日,多次参加爱国华侨组织的“一碗饭运动”,为抗战和救济难民捐款。
博士毕业后,马大猷面对祖国山河破碎,工业基础薄弱,科研水平单薄,迫切需要人才的现状,立刻踏上归途,返回燃遍抗日烽火的祖国,选择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,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。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,马大猷生活简朴,住在“望苍楼”前院大约10平米的小屋里,屋内的陈设只有床、书桌、书架和盥洗用具。
马大猷为人正直,爱憎分明,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袭击,他挺身而出,声称自己是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的负责人,严厉斥责对方并要求立即离去。马大猷保护教学环境和师生安全的正义行为,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和敬佩,也为学生们树立了榜样。

马大猷(右三)在西南联合大学
敢于对“大家”的理论说“不”
马大猷对待学术研究总是认真仔细,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,他围绕国家发展“两弹一星”的战略目标,先后开展了核爆炸侦察和声学探测、大气层核爆炸的次声监测等一系列重要研究工作,为开拓中国现代声学事业打下坚实基础。
马大猷即便在繁忙的科研事务管理中,也不忘保持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求实精神。莫尔斯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理论声学家之一,马大猷的导师亨特就是在莫尔斯的理论影响下,开始与学生们(马大猷和有“美国声学权威”之称的白瑞内克)作矩形室内的声衰变分析的。1989年,马大猷就指出莫尔斯的室内声场经典简正波解中,应当加入代表直达声的一项,使其物理意义更加明确。对这个问题,马大猷似青年科学家一样尖锐直率,他批评莫尔斯的室内受迫振动理论“只有数学,缺少物理”。他认为,莫尔斯没有认真分析声源的作用,就贸然投入数学处理。实际上,他的批评不完全是针对莫尔斯,也是提醒更多只注意改进模型算法而忽略物理分析的青年学者。
不说客套话,只说心里话
1962年2月,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。马大猷出于对国家大事的关心,在物理组的小组会上率先大胆发言,促成对知识分子的“脱帽加冕”。马大猷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,众人称赞马大猷的这一举动为“一马当先”。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还在中国科学院的会议上表扬马大猷,说他不说客套话,只说心里话。陈毅副总理在3月5日和6日,分别向会议代表宣布,要为知识分子“脱帽加冕”,也就是脱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之帽,加“劳动人民知识分子”之冕。
马大猷是一位治学严谨的科学家,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。他一直十分关心科学教育事业,坚持理工结合的教育思想,注意培养青年学者的理论素养和动手能力。“有时看到一些科学家为引进日本产品还是德国产品而争论,我脸都红了。”这是马大猷的话语。他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性,他曾经说过:“自然科学研究中,以创造性劳动取得的发明才是评价标准,科学只承认第一,不承认第二。”
即便在耄耋之年,马大猷也积极建言献策。他上书国家,呼吁要加强基础研究工作,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不断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,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不断努力。